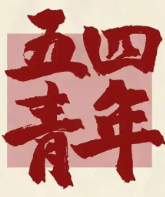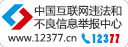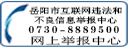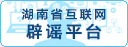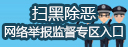岳陽學院教師 劉著之
2018年,作為記者的我捏著錄音筆站在湘西一座百年祠堂前,耳機里循環著采訪對象的方言:“我們的事,你們寫字的人不懂。”那一刻,我想起費孝通在《鄉土中國》中所言,“語言像是個社會定下的篩子”,而鄉土的經驗是比篩孔更細的粉。
《鄉土中國》是費孝通先生1947年基于田野調查寫成的社會學經典,以十四篇短文解剖中國基層社會:從人際關系如水波紋般由親及疏的“差序格局”到依靠傳統習俗而非法律維持穩定的“禮治秩序”,從“文字下鄉”的困境到“長老統治”的機理。一部小冊子,卻猶如一雙大手,剝開中國鄉土社會的肌理,露出其中千年來未被言明的文化基因。
初讀《鄉土中國》,我劃滿問號:“差序格局”不就是人情社會嗎?“禮治秩序”不就是封建殘余嗎?直到那天,我親眼見證了那場比法院判決更有效的祠堂調解——兩戶村民因宅基地起了爭執,可最后兩家的男人在祠堂門檻前蹲著抽完一袋煙,族老把他們的酒碗碰在一起,酒液濺在族譜上,像又添了一代人的印記。原來這就是“無訟”傳統的現代適應性,一如書中所言“鄉土社會的權力,是教化性的”。
當都市人慣于用各種現代化標簽簡化鄉村時,我們忽略了一種更細膩的“算法”——它計算的不是產權面積,而是世代相鄰的情分權重。
這也成為我職業生涯的轉折點:不再用“落后/進步”的二元框架自以為是地解讀鄉土,而是學會理解它自洽的邏輯——就像費孝通筆下的差序格局,看似不夠“現代”,卻維系著無數村莊的呼吸與心跳。
如今,當我轉換身份,站在講臺上,給我以啟發的,則是《鄉土中國》里那句“文字是廟堂性的”。我告訴學生:“你們要做的,是把祠堂里的故事‘翻譯’給流量時代。”我致力于思考,如何更好地教會年輕一代用新技術去守護舊靈魂。
譬如,以往指導新聞專業工作坊時,我們放任學生自選題材——美食探店、城市夜跑、電競比賽……雖然鍛煉了技術,但總感覺少了些什么。直到重讀《鄉土中國》,我發現費孝通早已點破——“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”。我意識到,當00后們用4K攝像機追逐都市光影時,鏡頭背后那片更遼闊的土地,正逐漸失語。
我想,下一期工作坊,我們是否可以聚焦鄉村振興報道,只允許報道縣域以下題材(非遺傳承人、返鄉創業者、村級“土專家”),并重構一些“鄉村振興報道工作坊”的規則:如48小時駐村,睡農家的硬板床,吃灶臺的柴火飯;上幾堂方言聽力課,聽農村老人用土話講述鄉土故事,再翻譯成短視頻字幕;開展反哺式創作,作品必須給被拍攝者審核,修改至他們點頭認可……
值得欣喜的是,我們文學與傳媒學院的廣告學專業今年擬新增“鄉村振興廣告傳播方向”,這與我通過閱讀而產生的思考不謀而合。未來,我計劃參與兩項研究實踐,一是參與鄉土品牌的傳播研究,和學生一起探尋將富有湖湘特色的各種“土特產”變成“文化IP”;二是助力產學研聯動,與本地文旅部門展開合作,把學生分組“承包”到縣域,要求他們用幾個月時間,為某個村鎮量身定制從抖音腳本到農產品包裝的傳播方案。
書中說,文化得靠記憶,不能靠本能。而我們的使命,就是幫助年輕一代在流量時代,重建對土地的記憶能力。偶爾在講臺上,我會想起湘西祠堂里那盞被風吹動的油燈。費孝通在1947年用鋼筆素描的鄉土,如今我們和學生正用鏡頭重新顯影——那些被都市人稱為落后的紋路:方言的韻腳、農具的木柄、葬禮上揚起的泥土,都將成為未來傳播學的“源代碼”。
我希望,今后的日子,在岳陽學院的實訓室里,我們不做文明的判官,只做時空的接線員:讓祠堂連接直播間,讓米酒碰撞二維碼,讓祖輩的智慧永遠在線。教育的真諦或許就在這里——我們教會學生使用攝像鏡頭,而土地教會他們,什么值得被看見。
(本文系岳陽學院首屆“世界讀書日教職工讀書征文活動”一等獎作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