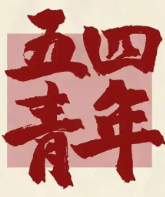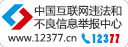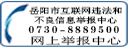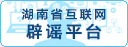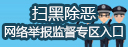□江哮
去年11月28日,收到晏宏打來的電話,說南湖新區文聯要籌拍《二十四節氣里的南湖—冬至—橋》紀錄片,要我提供一些關于三眼橋的資料。既然蒙晏主席抬愛,我自然卻之不恭。煲電話粥時,我說,僅僅只拍三眼橋顯然分量不夠,當年捐巨資修三眼橋的主人,墓園蕭條,無人問津,是否可以給幾個鏡頭?于是,就有了拜謁鐘謙鈞墓的約定。
我與晏宏多年前有過共事的經歷,她辦事果斷,雷厲風行。果然,12月2日剛上班,她的電話再次響起,約好下午兩點半過來接我,于是,與黃去非教授、吳窮、李萍等人欣然向黃沙灣進發。
鐘謙鈞(1805年—1874年),字秉之,亦字云卿,巴陵樓西灣人(今岳陽君山柳林洲人)。他自幼機警聰敏,入私塾讀《論語》《大學》,皆能述其要義。據《鐘謙鈞墓志銘》(時任岳州知府張德容撰)記載:“家貧,為糧舟主計,為其資供父母甘脂。”因緣際會,他因打得一手好算盤,被人帶到京城“作計”,由此開啟了命運的逆襲之門。道光二十四年(公元1844年),時年39歲的鐘謙鈞捐資以從九品分發湖北試用,由此涉足官場。咸豐元年(公元1851年)授沔陽州鍋底司巡檢,五年后升知縣。同治元年(公元1862年)授漢陽知府,不數日即調辦糧臺,兩年后賞加鹽運使銜。同治四年(公元1865年)調任武昌知府,以功晉一級官階。同治八年(公元1869年)升廣東鹽運使。同治九年(公元1870年),加按察使銜。同治十一年(公元1872年)正月,署按察使;七月,賞二品頂戴。同治十二年(公元1873年),因病乞休。
鐘謙鈞急公好義,對地方公益事業,總是慷慨捐輸,“作宦二十余年,所得俸銀薪貲,悉以為利人濟物之用,而自己無私積焉”。(摘自《鐘謙鈞墓志銘》)晚清臨湘人吳競(吳獬侄孫)在其《豆棚人語》中說鐘謙鈞“一生薪俸所入盡于此”。鐘謙鈞捐資義舉不勝枚舉,簡單梳理一下,大致可歸納如下:
同治元年,捐俸(數目不詳)倡修漢口晴川書院;同治六年,捐銀二千兩充陜甘軍餉;同治八年,捐銀千兩修復粵東禺山書院,募銀二萬三千兩主持修復粵東菊坡精舍;同治九年,湖北水災,他“以九千金寄當事為賑恤之”;同治十一年,以養廉銀二萬兩匯直隸,作為天津賑款;同治十二年,以養廉銀二萬兩匯陜甘后路糧臺,作為甘肅賑款。以上是見之史乘的鐘謙鈞在外省捐資情況。
對于桑梓之地,他著意尤多,捐資不斷,影響深遠的主要為:同治八年,捐銀四千兩修建君山樓西灣文誼莊義塾;同治九年,捐資設立南津港義渡;同治九年,捐銀“萬二千緡”(即一萬二千兩白銀)重修岳州考棚;同治十年,因夏秋大荒,捐銀五千兩,買谷五千余擔存城中備荒;同治十一年,捐(數目不詳)建巴陵七里山寶塔;同治十二年,捐銀三千兩加固岳陽樓基,重修宸翰亭;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捐銀兩萬八千兩重修三眼橋……
同治十三年(公元1874年)農歷二月二十三日,鐘謙鈞星隕,葬于南津港獅山之南。噩耗傳出,同郡頭號人物、正在甘肅平定回亂的左宗棠上書朝廷,厚贊他:“歷官楚粵,循聲卓著,應……咨送史館,編入循良傳,以存其人。庶該故員清風惠聞不至湮沒無傳,而于國家獎廉勵俗之意益有合也。”同年十二月初四,同治帝御批:“已故廣東鹽運使鐘云卿謙鈞,歷官湖北、廣東等省,廉惠宜民,輿情愛戴,并捐廉資助賬款尤屬急公,著湖廣、兩廣總督,湖北、廣東各巡撫即將該故員事跡查明,咨送國史館立傳,以昭激勸。”“國朝二百余年,入循吏傳者二十有四人。湖南溆浦嚴公如煜居其一,今得吾巴陵鍾運使,湖南始有兩循吏。”摘自杜貴墀《巴陵人物志·鐘運使傳》湖北士民將他恭入漢陽名宦祠祭祀,亦屬備極哀榮。在《重修巴陵三眼橋記》一文中,時任湖南巡撫王文韶充滿深情地寫道:“鐘君出而有濟于世,退而澤及其鄉,而又以補有司之所不逮,其行義有足摩世而厚俗者,茲橋其著焉者也……今逝者于斯矣,其澤無窮也。”
時過境遷,謙鈞公當年舉國仰慕的豪俠義舉,漸漸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之中。如果你在三眼橋邊隨意采訪市民,你知道三眼橋是誰修的嗎?他一定會指著橋頭那尊高大的青銅雕像回復你:方尚書啊,難道這還有錯嗎?就連嚴肅的文史專家,有時也會有意無意地忽略。而今,已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三眼橋,立于橋頭的《重修巴陵三眼橋記》刻碑早已無跡可尋。“三眼橋位于岳陽市南湖大橋西側,今南湖紫荊堤中段,因橋為三拱聯綴砌筑,故俗稱三眼橋。全橋基本呈南北走向,由花崗石砌筑,長56米,寬8.84米,通高15米,橋面由麻石板鋪墊,兩邊護以80厘米的石欄。橋兩頭各有石獅一對,栩栩如生。據記載,三眼橋由北宋慶歷年間岳州知州滕子京創建,明代大橋被洪水沖毀,在退休回鄉的尚書方鈍的大力資助下得以重建。清代又有多次修葺,石橋保存基本完整。2006年5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八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”由岳陽樓區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6日立碑的三眼橋《說明詞》是這樣寫的。
我不知這段《說明詞》出自何人之手,總體感覺就是除文理不通之外就是罔顧歷史真相。姑且不說文中“創建”二字搭配是否正確,“修葺”二字是否妥當,稍微對三眼橋歷史有研究的人都知道,從宋慶歷四年起至清同治十二年止,在八百多年的歷史中,三眼橋經過了修—圮—修多輪反復。滕子京所修之橋叫通和橋,又名堤頭渡橋或岳陽橋。明代從成化八年(公元1472年)到泰昌間(公元1620年)此橋先后六次重修,其中“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,邑人方鈍督修,名萬年橋(當時根本沒有三眼橋之說,筆者注),簡略,不帀歲輒墜。”清代從順治十二年(公元1655年)到同治十二年(公元1873年)也先后進行了四次重修(嘉慶八年,巴陵知縣陳玉垣募修未就),保留到現在的三眼橋是邑人鐘謙鈞捐銀兩萬八千兩,郡守張德容、知縣潘兆奎主持重修的。《說明詞》給人的印象是尚書方鈍重建后,該橋一直傲然屹立在南湖之上,清代只是進行過多次維修而已。這簡直是在信口雌黃,顛倒黑白。方尚書當年督修的萬年橋,“簡略,不帀歲輒墜”,就連三眼橋這個俗名也是他去世后165年才有的,而真正捐巨資修筑三眼橋的功臣竟然在《說明詞》中找不到片言只字。
市委黨校那邊,謙鈞公第六世孫鐘鑄早在那里等候。獅山其實是甑壁山最西的一個山頭,穿過湖洲學校,鐘鑄領著我們從山腳一路向上攀爬。據他介紹,當年是有石級可通墓園的。可近150年過去了,王朝代謝,物換星移,哪里還有當年半點陳跡?獅山之上,人工杉大多已有碗口粗細,這些年,液化氣甚至天然氣早已普及,附近居民斷然沒有人進山砍柴了,杉林之下,荊棘遍生,枯枝密布,每前進一步都困難重重。好在有鐘鑄在前面開路,眾人連推帶拉,費了好大的周折才氣喘吁吁地爬至山頂。
趁小憩之際,一行佇立四顧,風景果然形勝。透過林隙西望,扁山歷歷在目,更遠處,君山隱約可見。眼下是枯水季節,洞庭湖雖瘦成了一道閃電,但絲毫不影響“氣蒸云夢澤,波撼岳陽城”的想象。在一小片開闊地邊,一塊青灰色的碑石孤零零地兀立在環合的竹樹和蔓生的荊棘之中,那就是鐘謙鈞墓了。當年堪輿大師說,此處系金線吊葫蘆風水寶地,可以綿瓜瓞而裕子孫。鐘鑄后悔來得匆忙,沒有帶任何工具,繞場走了大半圈,總算從墓后的荊榛亂草中探身而入,然后,徒手小心翼翼撥開荊棘,辟出一線通道。眾人魚貫而入,但見墓地只剩殘碑半塊,碑后的墓丘已基本塌平,上面密生著盈尺的茅草,在冬日下略顯枯黃。一種莫名的傷感悄然涌上心頭,側目而視,但見同行者皆表情凝重,默然相向。鐘鑄說,此墓曾多次被盜,墓碑是在“破四舊”時被紅衛兵砸毀的。原來如此!沉默有頃,黃教授提議說,我們還是向先賢行個禮吧,于是,一行人比肩而立,恭恭敬敬面碑拜了三拜。
當晚,善詩的黃教授感慨系之,通過微信轉給我一首《謁鐘謙鈞墓》,茲錄如下:
甲辰冬月初二,與江哮、晏宏、吳窮、李萍諸友登甑壁山巔,拜鐘云卿墓。導游者鐘鑄兄,則云卿先生六世孫也。
不見當年馬鬣封,殘碑靜對夕陽紅。
漫尋雜草荊榛路,來話狂流砥柱功。
循吏聲名動曾左,鄉賢義舉比衡嵩。
古橋遙臥今如昔,還與行人憶逝翁。
來而不往非禮也,我搜索枯腸,奉和一首聊作回贈。
謁鐘謙鈞墓·次韻和黃去非教授
當年圣眷頻遷封,名列循吏史志紅。
慷慨無非澤梓里,凄涼戶邑忘勛功。
撫院橋銘迷典冊,尚書像塑賽衡嵩。
此日墓前徒扼腕,殘碑朽木伴賢翁。
文章發出后,岳陽名記劉衍清特意致電于我,說他在采風途中讀了拙文,對謙鈞公遭遇的不公,心有戚戚焉。晚上回來后,將有詩酬我。次日清早,打開手機,微信上就收到他的留贈。茲補錄于次:
步韻賡和黃去非、江哮倆先生《謁鐘謙鈞墓》
詩撥云破霧解塵封,終教遺賢映日紅。
曾播官聲傳鄂粵,盡傾俸祿積蔭功。
奈何精魄冷荒麓,未有松廬憩岱嵩。
桑梓諸君共努力,銅琶鐵板祭鐘翁。
12月16日上午,受晏宏之約再次往謁鐘謙鈞墓。“那天下山之后,就聯系了飄尾社區的工作人員將進山的路做了簡易修整。”晏宏言語中略帶自豪,“今天下午市文旅廣電局文物科科長歐繼凡將帶相關人員前去踏勘。”黃去非教授教務繁忙未能同行,但拜謁者增加了鐘明楚(鐘鑄之父)、紀錄片攝影師柳慶年和兩名社區工作人員。走進湖洲學校,巧遇老同學楊槿,他在這里工作近二十年,才從校長崗位上退下不久。于是,邀他一同進山。
“真的是太不應該了,今天才知道學校后山安葬了這么一個了不得的人物。”進山的路果然好走多了,楊校長與我一路攀談,似乎有點自責,但很快就托出自己的規劃,“鐘謙鈞的事跡確實值得弘揚,以后要常態化帶學生上來祭拜,作為學校傳統文化教育的一項活動開展。”“這個提議蠻好!上面不是要求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嗎?愛國先愛鄉,講好岳陽故事,我覺得將鐘謙鈞的事跡編入貴校的鄉土教材也未嘗不可。鐘謙鈞生前到處捐資辦學,比如倡修漢口晴川書院,修復粵東禺山書院、菊坡精舍,修建文誼莊義塾,重修岳州考棚。還捐資為同鄉林文竹刻印《四書貫珠講義》,重刊《阮本十三經注疏》《通志堂經解》《古今解匯函》《小學匯函》等書籍。”我邊掰著指頭細數鐘謙鈞為教育辦的一系列實事邊說,“有這樣一位前賢護佑,說不定貴校會一飛沖天呢。”朗朗的笑聲在松間回蕩,我慶幸今天來得真是時候。
鐘明楚年近七十,是謙鈞公五世嫡孫,歲月的無情刻刀在他臉頰上鏤出了道道深淺不一的溝壑。說到謙鈞公,他有講不完的故事。他說,這塊墓碑是在獅山半山腰的一條溝邊發現的,估計是造林人鋪在那里作橋用。1983年清明前,他組織家族的二十多個勞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抬上去的。他說,謙鈞公的錢都捐出來了,墓穴中其實沒有什么陪葬品,值錢的就是一掛朝珠,聽人說被一羅姓掘墓者私吞了。他還說,謙鈞公墓前原有一對石獅,跟三眼橋上的造型差不多,后被人放在飄尾電影院門口,已好些年冇看到了,估計早就跑了路……明楚先生還領著我們看了幾塊從墓園中散落下來的石件,其中一塊是墓碑上的頂蓋,一塊槽形的石器不知用途,另一塊是墓園四至的界樁,上書“鍾東界”。
下山途中,明楚先生說了很多感激的話,末了,他話鋒一轉:“謙鈞公的墓園被糟蹋成這個樣子,作為他的后裔,我們心里很憋屈,也覺得臉上無光。但又有什么辦法呢?有心無力哦!我現在黃土都埋齊頸了,唯一的請求就是希望政府能把謙鈞公的墓園修起來,畢竟他當年為地方還是做了很多好事的!”
一路無語,我真的不知該怎么回答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