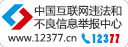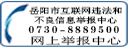□曹利華
那些年,我們華容花鼓戲是春節期間的傳統娛樂節目。在東洞庭湖畔的平原地區,湖區人乘著氤氳水汽,勞作一年,終于洗腳上坡,到了舒坦一口氣的時候。那時電子產品沒成氣候,影視還沒有規模化地來到民間,再說,屏幕上的人畢竟是假的,不比花鼓戲有血有肉的真人在面前晃動,伸手可觸。這就注定花鼓戲要擔當娛樂大頭了。
鞭炮炸裂,鑼鼓緊隨其后響開了。我們這些孩子捂緊耳朵,根本不怕死,鞭炮再響,危險再怎樣在炸裂里潛伏,也抵擋不住花鼓戲的誘惑。大人小孩蜂擁而至,那個熱烈與擁堵是現在見不到的鄉下大場面。很多人在城里過年,綿綿鄉愁在一只虛擬的碗里彌漫滋生。“濃妝艷抹”的食品擺滿了精致的餐桌,卻掩不住一雙迷茫的眼睛望著遙遠的故鄉,一段轉彎抹角的花鼓唱腔在體內行走,那種再也回不去的愁緒,像看不見的絲絲縷縷,在城市上空游走。
路上的茅草纖細漫長,土路牽手連到各戶門口。不像現在路面光光的,很難看到茅草飄拂和行色匆匆的腳步。葉片拂拭著看戲人的腳,也拂拭著花鼓戲演員飄逸的戲服。紅紅綠綠的嶄新綢布也吻著飄搖的茅草。綢布服裝在當時是很珍貴、時髦的。但再貴也下決心買起。畢竟一年就這一回。而且領著演員上門的師傅也很想露一手。
花鼓戲演員完全出自草根,是土生土長的本村人。正是那些為數不多的師傅藏著一肚子戲文,平常太忙了,根本無法排解耕作的緊繃與辛苦,那滿肚子戲只能在夢里開演,觀眾與演員僅他一人。現在想來,這些民間稀有的花鼓戲導演,是真正的本土大師。應當說花鼓戲的娛樂化普及與深厚的文化傳承,是真正來源于這些草臺班子,來源于艱辛的勞作歲月里還心心念念著戲的人。
年紀大了,上不了臺面,須得年輕人來接這趟戲的班。師徒口口相傳,腳本自在胸中,他們是真正的花鼓戲唱作人,在當地享有很高的威望。就像一顆在民間游動的米粒,起初以谷的形式入泥,收獲時仍是一顆披著黃金外衣的米粒。花鼓戲師傅的“母粒”來自民間土壤,自生自滅卻蓬勃興盛,用不著刻意培植,便在湘北各地開枝散葉,花開萬朵。
正月初,過完大年,道路上充斥著絡繹不絕的拜年者,之后,戲便上門開唱了。絕大多數家庭是從心底里歡迎的。盈門的喜氣還沒揮發殆盡,對聯從大門的兩側散發出紅彤彤的喜悅,一點文化氛圍經過聯語一提醒,便是正月的畫龍點睛之筆。更兼花鼓戲的到來,把過大年的興頭推向高潮。
一聲婉轉至極的嗓子,從遙遠的戲文里透出來,那是千百年的時光流轉,經過許多代人的精心打磨,有了湘北方言的俏皮與北方官話的摻雜,華容花鼓的味道更是十足了。花鼓戲從亮麗的舞臺來到真正的民間,一家一戶,并不需要精心挑選、準備,只需要準備幾毛錢或一個花根雪棗包,或者一包幾毛錢的煙就行了。
這是民間最純粹的嗓音。在平常至極的人家養育,又在平常至極的人家開花,一開嗓就能贏得滿堂的吆喝。正像一個男人,抱著幾畝田就能安然度日。他們不想上天堂,只想過粗茶淡飯的日子。連花鼓戲都那么接地氣,流動的舞臺隆重地搬到了各家的堂屋正中央。
家家開唱,戶戶余音,繚繞在燕子瓦擱置的房梁間,還有鞭炮直入肺腑的濃香幾日不散,似乎正月的喜氣殷勤地挽留住了它們。那些優美的旋律與婉轉的唱腔更是在心頭縈繞作響。
熱鬧的大年走了,像一位和顏悅色的親戚,萬分舍不得卻不得不松手。行云流水般的花鼓,一頭連著勞勞碌碌的過往,一頭又開啟撲面而來的嶄新一年。油菜花就要從沉悶一冬的土縫中噌噌冒出,艷艷桃花正思謀著從枝上的突起里跳脫出來,而花鼓戲則重新回到了再普通不過的、帶泥塵的夢中。